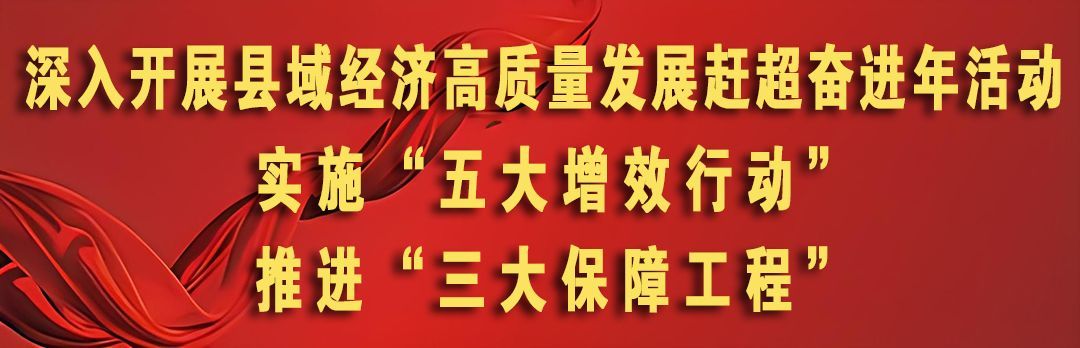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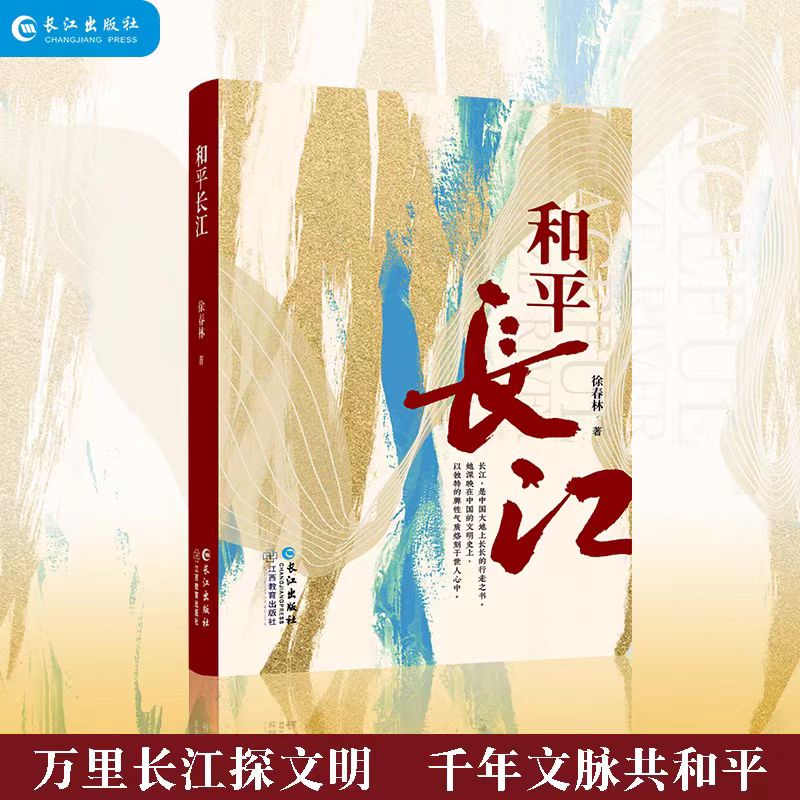
长江,是中国大地上长长的行走之书。它深映在中国的文明史上,以独特的脾性气质烙刻于世人心中。
——笔者记
在数千年的中国文化历史长河中,长江、黄河,一南一北,盘桓在中国广袤的疆土上。
我们一眼便能辨识长江,远古生活在长江岸边的先民是这样,今天的人们依然是这样。这不是我们目光锐利的缘故,而是长江一直保持着自己的面庞。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她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奔流而下,穿过山高谷深的横断山脉,劈开重峦叠嶂的云贵高原;奔腾的江水一出三峡,便一泻千里,在广阔的江汉平原上驰骋奔流,最后注入浩瀚无垠的东海。
辽阔的长江流域有我国最丰富的资源、最富饶的沃土,几亿人口在她的怀抱里生息成长。
致敬伟大的母亲河——长江。
《长江源》(五)

我们离开沱沱河时,天空澄蓝,风飕飕地吹在脸上,有一种刺痛的感觉,太阳不知不觉从东边溜到了头顶。
第二站是昆仑山。
昆仑山是青海与西藏的分界线,海拔 5000 多米。
早晨七点从沱沱河出发,一直到接近黄昏才到界碑处,全程近 300千米。
一路上山峦错落,绵延起伏。黑色的山,石头裸露在外面,若明若暗。
地质和地貌的改变,似乎在提醒人们开始注意大自然与大地走势之间的呼应关系。朝前走,只见遍布着蜿蜒的河流和大大小小的水洼,湿润的风带着冰山的寒意从古老的水面上掠过。阳光照射下来,感觉那光芒来自地平线,把一切都照得通体透亮。
在高原上行走,虽然裹着厚厚的冬装,可还是冷得瑟瑟发抖。头顶棉花般的云朵镶嵌在深不见底的蓝色中,远处的天边却有乌云在聚拢。随着距离的拉近,逐渐看清乌云的正下方生出许多丝丝缕缕的黑色絮状物,那是雨,雨下得特别快,说来就来,闪电、雷、雨、冰雹一齐劈下来,让人猝不及防,顿时被刺骨的寒意裹挟。
傍晚时分,我们艰难地到达海拔 3200 多米的从昆仑峡谷流出的一条河边。
我出现胸闷、心慌等高原反应,平均心率达到了每分钟 130 次。尼玛潘多的阿爸把事先备好的氧气瓶给我吸了几分钟,感觉身心好了很多。
“昆仑山!”我听见有人喊叫。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
莽莽昆仑山,被誉为中华民族的“龙祖之脉”,昆仑文化被称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源。苍茫浩大的昆仑山横跨长空,犹如一条玉带将无数江河湖海揽入怀中。传说中的“千山之宗”“万水之源”、中原先民眼中的“百神居所”,无论是《山海经》《禹本纪》等上古文献,还是气势磅礴的古今诗词,都处处可见昆仑山的奇绝雄浑。
昆仑山是古老的褶皱山脉,全长达 2500 余千米,位于青藏高原腹地昆仑山脉和唐古拉山脉之间的长江源地区,平均海拔 6000 多米,分为西、中、东三段,西起帕米尔高原,横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西藏自治区,向东延入青海省西部,抵四川省西北部。其西段沿塔里木盆地南缘作西北——东南走向,这里山体巍峨,山势陡峭,高大的山体上分布着面积极为广大的冰川,风光绮丽,景象壮观。
我们的车停在昆仑山口标记碑旁。
在山下,用望远镜眺望着壮阔雄浑的自然风光,内心犹如那高低的山脉起伏着。
尼玛潘多从地上捡起一个石头给我看,石头很光滑,上面还带着一种黑色,然后又将石头装进背包里。“来过昆仑山,这就是纪念”。
公路上川流不息。沿路环保志愿者在这里建立了多个自然保护站。这里曾经是非法偷猎者的场地,野生动物的数量急剧减少。
1994 年 1 月 18 日,治多县西部工委书记杰桑·索南达杰为保护藏羚羊,英勇牺牲。为了纪念他,在昆仑山路口立有环保卫士杰桑·索南达杰纪念碑,缅怀这位为保护可可西里野生动物而捐躯的藏族优秀儿子。可可西里还建立了首个以索南达杰的名字命名的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站,也是中国民间第一个自然生态保护站。
青藏高原广袤辽阔,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相互依傍南北纵深。这里的天空紧贴着地面,云朵仿佛触手可及。澄澈的蓝天下是白花花的盐碱地和艰难生存的几株高原植物,雪山背后正酝酿着变幻莫测的天象,未知的风险在不远处随时可能降临。
从昆仑山口,我们驱车一个多小时,来到了一个叫不冻泉的地方。这里有一座迄今为止世界上海拔最高、穿越冻土层最厚、科技含量最充分、施工难度最大、空气最稀薄、条件最恶劣的高原特大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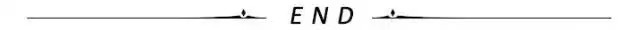
责编:周 保
审核:金三红
监制:罗正兵






请输入验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