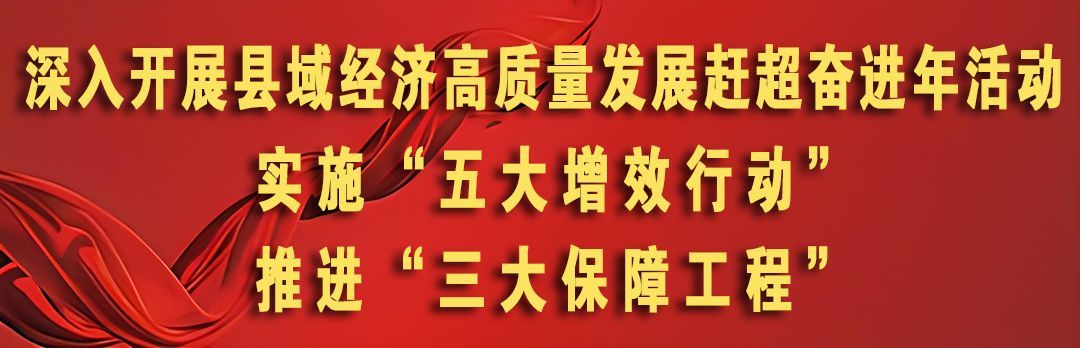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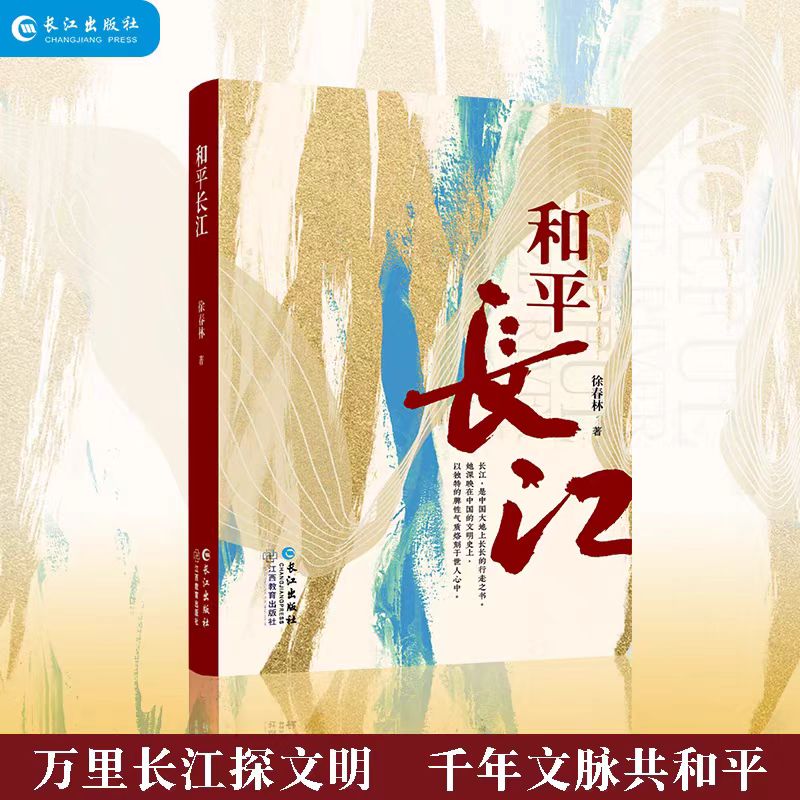
长江,是中国大地上长长的行走之书。它深映在中国的文明史上,以独特的脾性气质烙刻于世人心中。
——笔者记
在数千年的中国文化历史长河中,长江、黄河,一南一北,盘桓在中国广袤的疆土上。
我们一眼便能辨识长江,远古生活在长江岸边的先民是这样,今天的人们依然是这样。这不是我们目光锐利的缘故,而是长江一直保持着自己的面庞。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她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奔流而下,穿过山高谷深的横断山脉,劈开重峦叠嶂的云贵高原;奔腾的江水一出三峡,便一泻千里,在广阔的江汉平原上驰骋奔流,最后注入浩瀚无垠的东海。
辽阔的长江流域有我国最丰富的资源、最富饶的沃土,几亿人口在她的怀抱里生息成长。
致敬伟大的母亲河——长江。
《高原上》(五)

在高原上,各种各样的故事无时无刻不在上演。这里面也是善与恶的较量。大自然里弱肉强食是一种自然规律,而人与人却不同,人有道德和法律约束,就算弱者也有生存空间。
我突然想起,我还遗漏了一座叫色吾沟的废城。
这是 1952 年 10 月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成立时的县府所在地。1980 年 10 月,色吾沟因环境恶化而被废弃,新县城迁至 70 千米外的通天河更下游的约改滩。
这个有着“长江源头第一县”美称的县城,曾经的繁华和喧嚣、车水马龙在水源干涸面前消失,残壁上“为人民服务”的字迹在风雨侵蚀下更加斑驳。在大自然的淘汰中,没有任何例外可以逃掉。在生态灾难面前,
人终于无可奈何地退却了。
沿着牙曲村的小路向着索加乡驶去。索加乡有着良好的湿地和草场,众多的野生动物在这里栖息繁衍。这个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辖乡,有着 1 万多平方千米的土地。
湿地是江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像海绵一样,为江河涵养着大量水分,同时又是物种的基因库。在索加的沼泽地里可以发现一条弯弯曲曲的沟,这条沟宽不过半米,但底部的泥沙结实,被人们称为野驴河。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政府禁止猎杀藏野驴后,除了索加的君曲附近的藏野驴有所增加外,其他地方很难见到成群的藏野驴。这几年,由于气候原因,草场不断退化。同时,因沼泽干涸,昔日藏野驴的迁徙之路,已经显露无遗。
这些因素导致藏野驴的活动区域也在缩小,藏野驴与家畜共处一个草场的情景已不是新鲜事。
高原的阳光强烈地照射在充满水分的高原湿地。热气流裹着水汽猛烈上升,缕缕的白色水汽从大地直接升腾到云端,云层承接了大量水分后不堪重负,又变化为雨水和冰雹倾泻在湿地、冰川和草场上。如此循环往复,是中华水塔源源不断的生命所在。
我在一则文艺电视节目里看到这样的故事:
达瓦卓玛来自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的麦宿地区,这里与西藏的拉萨、甘肃的夏河并称为“藏族三大古文化中心”。2017 年,她从美国贝佩丝大学(Bay Path University)毕业后,回到家乡主理家族传承几百年的铸铜工艺“钦乐”,并创立了与该工艺同名的品牌。
在外求学,为的是造福家乡。达瓦卓玛说,尽管自己学的是市场营销与企业管理,但是内心最感兴趣的还是人类学与文化研究。大学时期,她拍摄了多部聚焦于藏族文化与艺术的纪录片,其中《善意的谎言》便是从寻找自家丢失的牦牛小牛崽开始,讲述了牧人与家畜的故事。她说,即便是她们这样不靠放牧为生的手艺人家庭,也会养几头牦牛,为的就是供自家吃喝。藏族人没有不喝牦牛奶和酥油茶的。
出生于我国西藏拉萨,后在尼泊尔等地长大的四郎曲珍也表示如此。
尽管自己小时候并没有长期生活在藏族聚集区,但同样是喝着牦牛奶、酥油茶,吃着奶渣子长大的,所以对牦牛有着很强烈的敬重之心。饮食,是藏族人走到哪里都“戒”不掉的文化烙印。她形容:“我觉得藏族文化归根结底是牦牛文化。”
荒野的冷峻和神秘,充满着人们无法摆脱的诱惑,它原始的空间里含蓄着大自然无尽的威严。人们在它面前会自然地放弃世俗的追求,重新寻找自己野性的生命力。
高原苦寒,在无法解释变幻莫测的自然现象却又必须观察、适应和依靠自然的年代,动物养育了人类,因此动物是有灵性的。同样,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也是有灵性的,人作为自然界的寻常一员生存于众生之中,与万物和谐相处,尊重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生命。由此,衍生出万物一体、万物有灵、万物为神的原始信仰。
站在海拔五六千米的广阔高原上,层层冰雪风雨,却不能阻隔万物成长的生命。我从萧瑟的北风中,看到傲立雪中的生灵,在万丈阳光下迎接春天。
环顾苍穹,天空一碧万里,白云触手可及。可可西里大漠孤烟的地方,奔跑的野牛卷起漫天烟尘,蹄声敲动着洪荒的鼓点,这是一首宁静和狂野的交响,你可以聆听到原野律动的脉搏。
这必然是一片充满野性的疆土,这里是生灵最后的家园。
我庆幸来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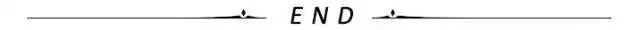
责编:周 保
审核:金三红
监制:罗正兵






请输入验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