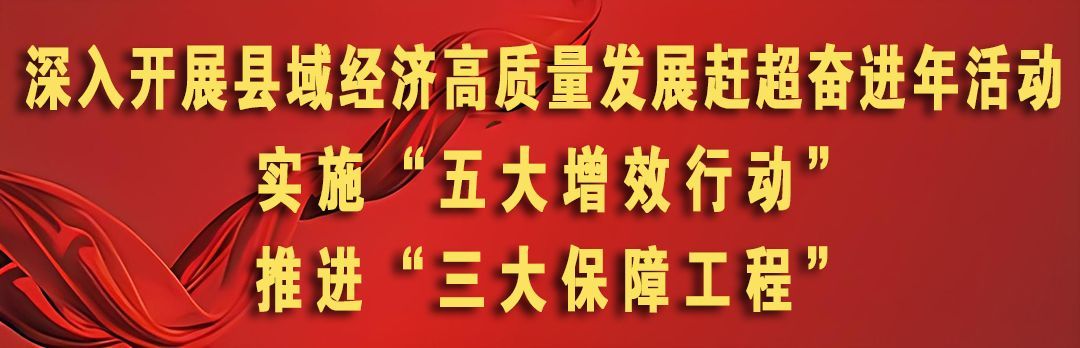


长江,是中国大地上长长的行走之书。它深映在中国的文明史上,以独特的脾性气质烙刻于世人心中。
——笔者记
在数千年的中国文化历史长河中,长江、黄河,一南一北,盘桓在中国广袤的疆土上。
我们一眼便能辨识长江,远古生活在长江岸边的先民是这样,今天的人们依然是这样。这不是我们目光锐利的缘故,而是长江一直保持着自己的面庞。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她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奔流而下,穿过山高谷深的横断山脉,劈开重峦叠嶂的云贵高原;奔腾的江水一出三峡,便一泻千里,在广阔的江汉平原上驰骋奔流,最后注入浩瀚无垠的东海。
辽阔的长江流域有我国最丰富的资源、最富饶的沃土,几亿人口在她的怀抱里生息成长。
致敬伟大的母亲河——长江。
《长江源》(十)

这次,我住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通天河畔的一个牧民家里。
牧民叫尼玛,42 岁,他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传统藏式建筑工匠,尼玛自小受父亲熏陶,对传统藏式建筑充满兴趣。尼玛的童年在放牧、种地、帮助父亲盖房中度过。
尼玛有着一副柔软的心肠,特别能体恤人,善解人意,也乐于帮助乡邻。
2010 年玉树地震后,尼玛看到家乡不少房屋在震中受损,他意识到保护传统藏式村落建筑迫在眉睫。灾后重建启动后,尼玛将事业重心放在传统藏式建筑和古村落保护上。他从头学习建筑行业基础知识,遍访玉树州境内的古老村落和传统藏式建筑,并前往西藏、四川、云南、甘肃等地寻访传统藏式建筑。尼玛对传统藏式建筑文化体系的了解不断深入,并积极参与保护通天河流域藏族传统村落的行动。
2015 年,尼玛在玉树州成立玉树古建筑保护协会,自费组织团队为分布在三江源地区的 100 多个古村落建立档案,基本信息涉及村落选址与空间布局、街巷空间与单体建筑、装饰特征与民风民俗等方面。
近年来,当地政府出台相关扶持措施,鼓励村民利用乡土建筑发展民宿、古村落生活体验区及观光旅游。尼玛积极参与古建筑修复,并帮助当地村民打造古村落生活体验区,吸引众多游客在传统村落中体验独特的民风民俗,传统藏式建筑和古老村落的巨大价值逐渐显现。
“房子是有生命的,但房子里没有人了,它的生命也就结束了。”尼玛最大的愿望是让传统藏式建筑工艺在保护中发展,留住古村落的印记,传承传统藏式建筑工艺,为每一个传统村落赋予新的生命。
住在通天河脚下,保护通天河也是尼玛的责任。尼玛的家里养着一只藏獒,藏獒在青藏高原一直具有神一般的地位。藏獒不仅是家兽,还是一种高素质的存在,是游牧民族借以张扬游牧精神的一种形式。如果不能让它们奔驰在缺氧至少 50% 的高海拔原野,不能让它们啸鸣于零下 40℃的冰天雪地,不能让它们时刻警惕十里二十里之外的狼情和豹情,不能让它们把牧家的全部生活担子扛压在自己的肩膀上,它们的敏捷、速度、力量和品行方面的退化,都将不可避免。
“狼已经不多了。”是的,狼已经少了,虎豹熊罴也都少了,少了敌人的藏獒,其天性又岂能不少?
秋天的高原不只是单纯的金色,更像是雨后彩虹,给人带来心灵的洗涤。在蓝天的映衬下,金色的树林显得格外美丽。大自然正用画笔勾勒浓墨重彩的世界,远山近水,等我们赴一场难以抗拒的秋色诱惑。
2022 年的冬天,我再去昆仑山。那是我第四次上高原,这次我是乘车路过。那个黄昏,我眺望着被余晖染成金色的昆仑山。山体已被一种雾气笼罩着,山和天黏合着,中间见不着分界线,山体被照得特别透明,河流像是块状的,各种分布式流动,不会有明显的沟壑,裸露的部分见着生命。
面对着这样的一幅图景,很快就会沉醉。
天气潮湿,温度大约到零下 10℃。群山里只闪烁着一点点空隙,仅够水流穿过。我被风雪包裹着,从山的那边,雪的那边,林的那边,传来几声乌鸦的叫声。我觉得那叫声是来自岁月之外的,在我童年的时光里经常会听到这个声音,最终这个声音钻进了我的灵魂。
我看到葎草抱紧了一株赤杨,脑子里便想,这株树因何干枯,是葎草使树枯死,还是因为树已经枯干葎草才出现呢?
一整夜睡得不好,骨头像散架了,照这样子明天再也走不动了。支气管炎越来越严重,我只能坐着过夜。湿漉漉的空气钻进来,感觉就像是要穿透身体。身体实在是受不了,我想得找条近路返程了。
第二天,太阳出来了。昆仑的西段山脉就像是一幅油画。只有简单的两种颜色,黑色和白色,山体的白就像是涂料堆积着,黑相对自然一些,显然白色是昆仑山的象征。白色的雾就像是浓烟,围绕着山体。那一层颜色里,历经着时间的轮回,让荒凉变得更有力量。
第三天,然而,让人惊叹的是另一幅图景:在大大小小的沼泽旁,几只藏羚羊低着头在地上吃着草,一些高原植物在寒冷的环境中顽强生长,为生活在此地的动物提供了充足的粮食。于是一个又一个关于生命、关于力量、关于野性的故事在这片广袤荒野上流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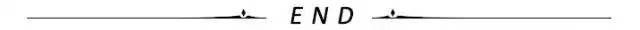
责编:周 保
审核:金三红
监制:罗正兵






请输入验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