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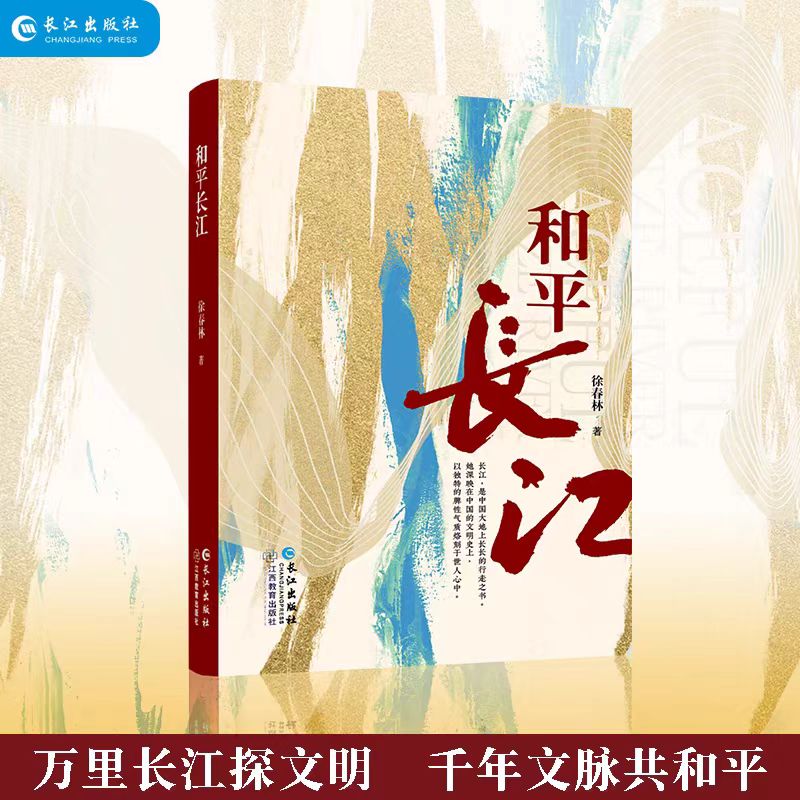
长江,是中国大地上长长的行走之书。它深映在中国的文明史上,以独特的脾性气质烙刻于世人心中。
——笔者记
在数千年的中国文化历史长河中,长江、黄河,一南一北,盘桓在中国广袤的疆土上。
我们一眼便能辨识长江,远古生活在长江岸边的先民是这样,今天的人们依然是这样。这不是我们目光锐利的缘故,而是长江一直保持着自己的面庞。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她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奔流而下,穿过山高谷深的横断山脉,劈开重峦叠嶂的云贵高原;奔腾的江水一出三峡,便一泻千里,在广阔的江汉平原上驰骋奔流,最后注入浩瀚无垠的东海。
辽阔的长江流域有我国最丰富的资源、最富饶的沃土,几亿人口在她的怀抱里生息成长。
致敬伟大的母亲河——长江。
《高原上》(二)

在青海柴达木盆地小柴旦湖的湖滨砾石层中,在海拔 4000 米以上的沱沱河沿(是格尔木市唐古拉山镇的驻地,青藏公路上的司机俗称它为沱沱河镇)及可可西里地区,采集发掘出一批打制石器,被确认为距今 2.3万年的旧石器时代生活在这里的原始人的遗物,他们被称为“小柴旦人”, 属中国远古文化的新人阶段。
我很好奇,沱沱河沿的“小柴旦人”是怎样生活的呢?
在无休止的风雪中,他们怎样避风、御寒以取得食物而生存下来呢?
藏族同胞认为山是神山,湖是圣湖,一草一木皆有生命。时至今日,牦牛仍旧是游牧生活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牧民需要家养的牦牛完成四季的牧场迁徙;游牧生活必不可少的黑帐篷则由牦牛毛编织而成,给了牧民一个个可移动的家。此外,人们的衣着、家中储存粮食的口袋乃至生活里的装饰用具,均取自牦牛的皮毛。饮食方面,肉、牛奶和以此为原料的奶茶、奶渣、酥油亦依赖于牦牛。几千年的漫长时光里,牦牛与牧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就连它的粪便,都转化成了生火的原料。他们用简单的方式维持着自己的生活,用泥土和石块盖房子,用自己的信仰与生存之道维系了高原生态的和谐与平衡。
牦牛全身是宝。
《山海经·北山经》中说:“又北二百里,曰潘侯之山……
有兽焉,其状如牛,而四节生毛,名曰旄牛。”
到了 7 月,气候暖和多了。有阳光的日子,“小柴旦人”一边晒太阳,一边捉身上的虱子之类的小虫,一张巨大的野牦牛皮也会被拖出洞穴吹晒。
孩子们钻到牦牛皮下玩耍,由此有了帐篷的最初构想,把野牦牛皮用树干撑起来,边沿用石头压着固定。有些日子,“小柴旦人”便从地下住到了地面。为了方便生活,又从沱沱河捡来一些石头、木条,用以存放或晾晒食物,这便是沱沱河人最初的家具物什。
在长江源头,老鼠和藏羚羊、野牦牛、野骆驼、野马、狼、狐狸一样,都是资格最老的居住者之一。它们在这里居住久了,也就适应了这里的一切。
老鼠对于先民们的贡献是,启发他们挖穴而居。在源头生态链中,老鼠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它们挖土打洞吃野生的果实,友好地让鸟雀在穴中占有一席之地。
在长江源头,有一片布满沼泽和一丛丛林木的荒野,现在也几乎没有村落。那时的人们害怕穿过荒野,只从小河里划船过去,在可以捕鱼和野兽出没的地方长期留住下来。
在干燥的河岸,可以放脚的地方,在清澈见底的水下沙土上,可见一层黑乎乎的东西。寻觅着人手加工痕迹的燧石、箭头和凿子。
为了追踪牦牛,“小柴旦人”还来到了玉树草原。
昆仑山及其支脉巴颜喀拉山呈东西向屹立于玉树以南。这里举目便是高山,视野中除了荒凉就是冰封雪域的宁静。
一日犹如一年,一日映射四季。一时明媚阳光,一时大雨倾盆,一时冰雹突袭。到过玉树的人,都会深切地感受到,玉树不仅是一个地名,更是一片无空无界的天。
青南重镇结古是玉树的重要组成部分。
结古是旧镇名,结古镇在很早以前是青海西宁、四川康定、西藏拉萨三地之间的重要贸易集散地。“结古”在藏语中是“货物集散地”的意思,长江从它身边流过,它也成了长江流域中第一个人口聚集的地方。
史料记载,民国初年,雅安每年发九万驮茶叶到结古,然后再由结古发五万驮至拉萨,其余四万驮在青海南部蒙古族、藏族聚居地销售。其实,玉树商业兴旺发达,结古镇有商号 200 多家,经营的货物中还有从印度经我国西藏转运而来的英国、德国、日本的货物。
现在的结古镇被现代建筑装点,影剧院、电视塔、酒楼、宾馆在“T”字形大街上展开,镇面积由原来的不足 1 平方千米扩展到 20 平方千米,人口也由原来的千余人骤增至几万人。腰间挂着藏刀的小伙子,带着几分粗犷与彪悍,和玉树草原在更大区域内的荒凉呼应着。奔跑的野马和野驴,在雪山下偶尔回首。

责编:周 保
审核:金三红
监制:罗正兵






请输入验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