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是中国大地上长长的行走之书。它深映在中国的文明史上,以独特的脾性气质烙刻于世人心中。
——笔者记
在数千年的中国文化历史长河中,长江、黄河,一南一北,盘桓在中国广袤的疆土上。
我们一眼便能辨识长江,远古生活在长江岸边的先民是这样,今天的人们依然是这样。这不是我们目光锐利的缘故,而是长江一直保持着自己的面庞。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她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奔流而下,穿过山高谷深的横断山脉,劈开重峦叠嶂的云贵高原;奔腾的江水一出三峡,便一泻千里,在广阔的江汉平原上驰骋奔流,最后注入浩瀚无垠的东海。
辽阔的长江流域有我国最丰富的资源、最富饶的沃土,几亿人口在她的怀抱里生息成长。
致敬伟大的母亲河——长江。
《高原上》(四)

驰骋的藏羚羊,是高原的一道亮丽风景。
藏羚羊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们曾是青藏高原上最庞大的兽群。20世纪 90 年代初期,超过百万只藏羚羊漫步在高原之上。
藏羚羊喜欢集群湖滨,有时会注视着湖水,不知道在想什么。当藏羚羊高速飞跑时,在平缓的荒原山坡,时速可达 80 千米。
每年的冬季之末,是藏羚羊发情交配的季节,也是它们比武大会召开之时,它们不约而同地来到荒原草甸集结,目光里有某些迫切,走来走去。
然后雄性藏羚羊之间便开始角斗,施展的是全部本领和各种招数,绝对不会谦让,雌性藏羚羊在一旁围观,等待强者的胜出。力挫对手之后的 1 只雄性藏羚羊,会带走 6 ~ 10 只母藏羚羊,到一个湖畔另觅住处,组成一个临时家庭。雌性藏羚羊妊娠的日子,刚好是可可西里最温暖的六七月间,这时曾经为了爱情作生死搏斗的雄性藏羚羊们,却团结组织起来前呼后拥地护送临产的雌性藏羚羊,至深山、峡谷隐蔽处生产。
乔治·夏勒,一位杰出的野生动物研究者,他曾多次造访青藏高原调查野生动物,并发出了保护藏羚羊的呼喊,向世界讲述了这个不忍耳闻的故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对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处五年、五年以上十年以下、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2021 年 3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再度介入野生动物保护:“违反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法规,以食用为目的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第一款规定以外的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陆生野生动物,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2016 年 9 月 4 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将藏羚羊的受威胁程度由濒危降为近危。
2021 年 3 月 21 日,护林员图丹东珠和格江在代曲村纳宗山下巡逻时,目击到一只全身披着土黄色长毛,拖着灰色长尾巴,像狼或者狐狸的动物在山坡上活动。格江介绍说,这只动物头宽、耳短而圆,面部鼓鼓的。格江随即按下相机快门。后经比对分析,确认该动物为豺,而这也是长江源头——通天河流域豺的首次正式记录。
在长江流域,豺仅在长江源、川西的甘孜及邛崃山还能安然度日。豺和其他野生动物一样,本身就有生存的权利。此外,豺是长江流域陆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之一。豺在我国并未彻底灭绝,2021 年,国家将豺由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升为一级。随着三江源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等保护地的建立,豺及其仅存的栖息地都得到了更好的保护。
天下大同,万物同生。
这是一片冷酷的土地。高原的阳光穿透稀薄的空气,凛风在冰雪上呼啸,冻土、冰川和雪山构成了严酷的生存环境,然而,生命依然在这里蓬勃繁衍。
青藏高原像一本博大的书,浓缩着地球和人类的秘密,那些飞禽走兽自由地演示着人类已经退化的生存秘密和技能,它们比人类更懂得如何阅读大自然。
河岸上风光如梦如幻,藏羚羊、藏野驴似惊魂闪电般奔跑起来。
远处牧民的帐篷升起袅袅炊烟,牦牛已经到了对岸的牧场。
放眼看去,两岸的沼泽在退化,沿途很多小支流干涸得露出河床,一些小水洼干涸见底,沙化出现,旱象渐重。目测不少小型湖泊和水网已经同长江失去联系。
我用相机拍摄到右岸有一只狐狸在喝水,却被一群守卫领地的赤麻鸭群起而攻之,左突右窜,最终被赶下河去。狐狸在水里狼狈地游着,后面一群赤麻鸭拍着翅膀追逐,嘴里发出快乐的嘎嘎声,可怜的狐狸失去了一个捕猎者在禽类面前的尊严,令人捧腹。
在这里我还见着一只体形圆粗、尾长的鼢鼠,它与我近在咫尺,我见着它那细小的眼睛里,布着一层银灰略带淡赭的颜色。它一点也不害怕我,就像是见着一个熟悉的人。
两岸草场有少量呈斑秃状,显出退化迹象。由于找不到合适的水源,我们只好靠岸。
天空还是一片阴霾,显得有些诡异。源区的许多地方,夏天是沼泽陷阱,不能进。
资料显示,可可西里由于受高寒强劲西风的影响,是全国的大风区之一。在风力较弱的季节,严重的高山缺氧以及多变的高原气候,使这里成了人类生存的禁区。
那天,我们走到了一个峡谷间的半山腰,阳光涂抹在峡谷的山头,慢慢由一线变成嫣红。与大山浑然一体的村庄里还住着很多人,见到外来的人,村里的老少像见到了外星人一样围了上来,但都不上来说话,一说话却又听不懂。正在着急,来了一个精瘦的汉子,说着一口地道的四川话,队伍里的四川人立即接腔,分外亲切。原来他叫陈来进,四川南充人,16年前入赘到这里,是这里唯一的汉人。
原来,10 多年前,陈来进和他十几个南充老乡一起来到青海修公路,认识了现在的老婆。听说这里没有计划生育,抱着多生几个娃的动机,陈来进就独自留了下来,生了 5 个孩子。
他在这里没有见到一个外人,没有听到一句乡音,也没有完全听懂妻子莫尼的藏语。
10 多年的时间里,他攒下了土坯房子几大间,牦牛 40 只,羊 70 只;他用内地的技术教会了村里的藏族同胞种马铃薯,教他们给青稞除草,带头盖温室种蔬菜。如今,他每年能收获青稞 2000 多斤,马铃薯 4000 多斤,是村里第一个买了卫星电视机的人家。
夜里,我们一起看星星。“你不想家吗?”
我的一句问话,陈来进半晌没有回答。他默默地看着星星,星星在我们上空静静地闪烁,仿佛在呼吸一样,仿佛发现了地上的我们,便微笑着,窃窃低语着,整个银河系,从星星到星星都洋溢着莫大的家庭欢乐。
“我不光是为了这个家庭,我还得守着这片高原。”陈来进说。
我和陈来进道别,他像个孩子一样紧抱着我,他的妻子莫尼带着孩子就站在不远处,我向他们挥手,此刻我把自己当作了陈来进的亲人,他的眼里布满了泪水,但没有流下来。
在返回的路上,我见雪地上留着一串狐狸的足迹。在弥漫着暴风雪的高原,狐狸在这里生活得悠然自得。我试着沿狐狸的足迹绕圈,一边数着进去和出来的足迹,直至数到与圆圈结合的最后一步,我还不知道,狐狸在这里是如何不见了踪迹。
黄昏时分,我们在半路停歇时见着远处有一个亮着灯光的小屋子。听说这里面住着的是位守藏羚羊的人,我们决定上门去看看。
房间整洁干净,我走进屋子,老人用冷峻的眼神看着我,一只手兜着烟斗,另一只手擦了下嘴巴。墙上挂着废弃的猎枪,旁边还有些没有用完的火药。他是一个老猎人,在不该打猎的时间,打死了一只动物,后来他成了藏羚羊守护者。我们再次谈论他的问题时,从那个隐秘的故事里,还是感到了他内心的酸痛。老人的老伴那时已经活不久了,所以他铤而走险。
这看似荒谬,却是温暖的。要知道,人与动物较之,我们多么希望人是高贵的。“请原谅我。”老人说。他承认,多少年以后,他的内心十分不安。
受过这等折磨的人,我相信他的内心是清新的、纯洁的、诚挚的,也是有力量的。在老人视力衰退的时候,他把自己简单的生活,用一种严峻的方式刻在地上。在高原的某一处,听见老人的声音时,他在呼唤着藏羚羊。
老远会看见黑压压的羊群在奔跑,向前或向着远处的山川奔跑,直到消失。
到这,突然就变得好理解了,人的本身是在平静中向前的。即便是一个老人,
他依然需要向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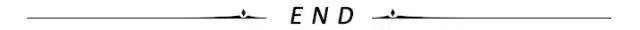
责编:周 保
审核:金三红
监制:罗正兵






请输入验证码